长摘要-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投资决策和金融资产配置
《世界经济》2020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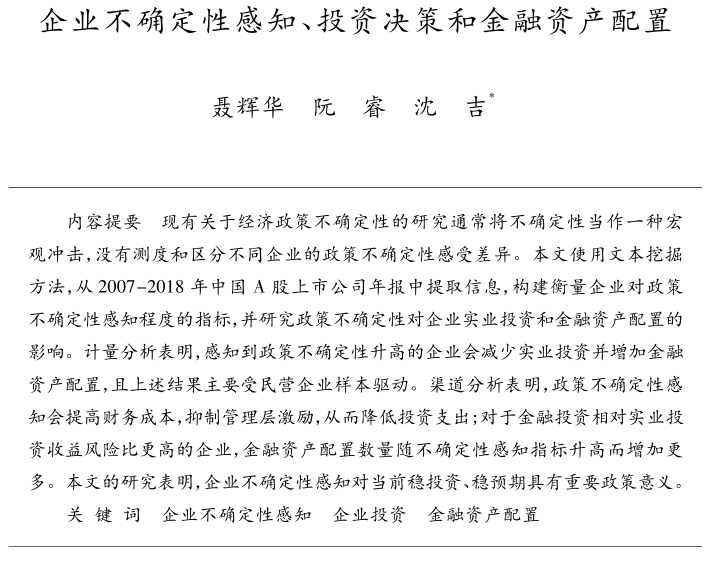
注:这篇文章首次构建了中国的企业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企业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主体,需要根据未来的期望成本和收益进行决策。政府的经济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如果经济政策频繁变化,会给企业带来困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宏观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Julio和Yook,2012;Wang等,2014;Gulen和Ion,2015;Crowley等,2018)。
第一类文献使用股票市场的隐含波动率(VIX)衡量宏观层面的经济不确定性(Bloom,2009)。但金融市场波动和实体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很大差异,例如杠杆率变动会引起VIX变动,而经济不确定性却可能没有变化(Ozturk和Sheng,2018)。第二类文献利用外生事件,并结合企业对这些外生变量的依赖程度衡量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这些外生事件包括选举或国际峰会等政治事件(Julio和Yook,2012;Kelly等,2016)、能源价格和货币汇率波动(Stein和Stone,2013)、贸易协定签订(Handley和Limao,2015)等。但是这些事件只能捕捉到不确定性来源的某一方面,而非全局的经济不确定性。即使是与经济政策相关的政治事件,也只能捕捉到一部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第三类文献使用基于新闻文本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例如Baker等(2016)开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EPU ),其中包括中国分指数。类似地,Sheng等(2019)、Huang和Luk(2020)分别使用中国内地报纸文本构建了中国整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其中Baker等(2016)开发的EPU指数为学界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应用(Wang等,2014;饶品贵等,2017;张成思和刘贯春,2018)。
Baker等(2016)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EPU )推动了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但该指标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EPU指数是国家层面的,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对所有企业有且仅有一个观测值,无法区分企业个体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差异。由于EPU指数是时间序列,在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时,无法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里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因此难以完全排除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的影响。第二,当使用EPU指数时,往往假设所有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是同质的。但现实中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经济政策各不相同,这些地区和行业的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会有差异;而且个体预期的形成方式多种多样,即使面对完全相同的政策环境,企业的不确定性感知也很难整齐划一。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本文认为有必要开发一种衡量中国企业个体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异质性感受的指标。
构造企业个体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指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在奈特看来(Knight,1921),不同企业对宏观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感受有差异,这正是企业家精神的表现,也是企业经营业绩差异的重要来源[1]。其次,凯恩斯指出,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根本属性之一(Keynes,1936);个体根据其掌握的有限信息和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对未来状态形成主观预期并做出决策;个体间信心的异质性和互动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群体信心波动是经济起伏的根本心理原因[2]。再次,Bloom(2014)也承认,不确定性是微观主体的主观感受,不同微观主体感受到的不确定性是不一样的。
然而,目前几乎没有关于企业个体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指标。本文尝试使用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文本,提取指标衡量企业个体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文的做法有一定的文献基础:首先,从上市公司年报、盈利报告等文本中提取公司经营状况相关信息的做法已经被广泛应用。较早的研究通过衡量这些文本的可读性(Li,2008;Loughran和McDonald,2014)、语调(Feldman等,2010;Loughran和McDonald,2011;Davis等,2015)等获取企业实际经营的信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侧重从上市公司相关文本中提取特定内容,比如企业的竞争策略、经营前景和融资约束等(Hoberg和Phillips,2010;Li,2010;Loughran和McDonald,2014)。其次,Hassan等(2019)使用美国上市公司业绩电话会议文本提炼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指标,业绩电话会议和年报都出自公司经营者对当前客观经营状况的表达。最后,证监会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公司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并对年报行文的规范性、严谨性均提出严格要求。从以上文献和法规来看,本文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提炼用于衡量企业感知到的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标具有可行性。
本文使用文本挖掘方法分析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提炼衡量每个上市公司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指标( Firm-EPU ,此后简称 FEPU ),并分析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受如何影响企业的实业投资和金融资产配置。本文发现,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企业减少实业投资并增加持有金融资产。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抑制民营企业的投资并提高其金融资产配置,但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和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背后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受到逆周期经济调控政策影响更多,所以无法采取措施应对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财务成本、减弱管理层激励的方式,抑制企业的投资支出。本文还发现,即使控制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收益-风险比与实业投资的相对比例等外在因素之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仍能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本文还把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指标分解为国家(整体经济)、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比较三种不同来源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和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发现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只能解释企业投资行为变动因素的11.34%,即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并不足以解释企业投资行为在剔除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后的变动。在控制宏观环境变动后,行业层面和企业个体对整体不确定性冲击的异质性感知依然会抑制企业的投资行为。这一结果从侧面支持了构建企业层面不确定性指标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本文还发现本文构建的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指标有很好的外推能力,说明这一指标造成过度拟合问题的可能性较低。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构建了企业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这是一个衡量不确定性的新指标。既有研究中,外生事件和EPU仅能表示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无法衡量微观主体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受。本文通过挖掘上市公司年报文本,获取每个企业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从而弥补这一空白,为后续开展跨地区、跨行业或跨所有制企业的不确定性比较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有利于推进关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的深入研究。第二,本文揭示了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新机制。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实物期权机制和融资约束,而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经理人风险厌恶机制导致投资支出下降。第三,本文证实即使考虑到可能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外在因素,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仍然会对投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这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宏观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实体经济的微观作用机制。
[1]奈特从认知论的角度区分了两种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一种是行为人可以确定事件发生所遵从的唯一的概率分布(无论这种确定过程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种不确定性定义为风险(risk);另一种是无法度量的风险,连概率分布都无法明确给出,被称为奈特式的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后世一般将后者专门赋予一个新的概念,称为“模糊性”(ambiguity),Ellsberg(1961)提供的实验证据表明,受制于模糊这类不确定性的行为人可能无法对其偏好的状态空间形成唯一的概率分布。
[2]更丰富的实例和阐释见两位诺奖得主Akerlof和Shiller(2010)关于“动物精神”的通俗读物。